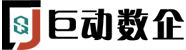知青周燕熙:上山下乡40周年回忆——尘封的记忆_历史_凤凰网
和毛泽东《卜算子·咏梅》
“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奈何笑容难为久,春来反凋残;残也不堪残,何须自寻烦,花开花落自有时,蓄芳待来年。”
想到需要写点回忆知青生活文字的文章,首先映入脑海的就是这首当年由三成兄酒后一挥而就,把一群曾自以为是能指点江山、激昂文字的天之骄子、却在一夜之间成为“接受再教育”对象的一代知青的处境、心态描写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的“和毛泽东《卜算子·咏梅》”。随之像电影一样一幕幕进入脑海的,自然应该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性格、信仰、前途、命运都产生重大影响,使我们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近两千个日日夜夜,以及伴随着这短暂而漫长的时日所发生的,已被记忆尘封在心底40年的一个个年轻鲜活的生命、一处处记忆犹新的地名、一桩桩琐碎难忘的往事!
一、愧疚
在几年的知青生涯中,曾发生过一件让我的灵魂得到净化,使我深感愧疚,终身难以忘怀的事情。
那是在1970年夏末秋初之际的中秋节前,当时我们点上的另外三个(周业奇、郑建平和我哥)哥们都回城过中秋节去了,我只身一人在点上孤独“留守”。本来就颇感被“人逢佳节倍思亲”的凄凉和孤独的氛围包围的我,在他们刚走后不几天,竟然鬼使神差般地在左大腿下方膝盖上长了一个小小的“疔”,也不过就是一、两天功夫,整个大腿,特别是膝盖部分疾速地肿得像水桶般大小,钻心的疼痛让人实在无法忍受,可更糟糕的是,恰好此时,我赖以生存的米缸里的米已吃完了。
那天下午,心情糟透了的我,正躺在床上捧着一本已被翻得破烂不堪的《普希金文集》,企图从中寻找精神上的支持和慰籍,以抵抗钻心的疼痛和饥饿的袭击时,楼上突然传来阵阵“劈哩啪啦”的声音--我们点的住房是队上的仓库,而楼上是队上堆放杂物的地方--本来就烦躁不安的我忍不住破口大骂:“×你妈,是哪个龟儿子在搞那样卵?”话音刚落,就听见“嘭”的一声,紧接着虚掩的房门被人撞开,只见队上的出纳兼保管老吴手执“扦担”,怒不可遏地冲进房间。一看此情,我心知不妙:“苗族不是最嫉恨被人骂娘吗?今天我死定了!”毫无反抗力的我只好闭上眼睛,等着挨揍。可半天也不见动静,睁眼一看,只见老吴手中举起的“扦担”已停在空中,眼睛盯着我肿得像水桶般大小的大腿--“老周吒(音,汉族老周的意思),你长'疔'啦?”此时他满脸的愤怒已变得十分和善可亲。紧接着,他坐在我的床边,仔细地观察我那肿胀的大腿:“不要紧,等我上山去给你找点草药,敷上去几天就好了!”几句话说得我眼睛水直在眼眶里打转转--这几秒钟时间情感反差的巨大变化,对我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
不一会儿,老吴就拿着已经舂好的草药,细心地给我敷上。见我厨房里不像煮过饭吃的样子,又去家中端来满满一大碗红苕和米煮的饭……
下午收工后,红云、红宝等一伙年轻的苗族兄弟听到我腿上长“疔”的消息,饭都没来得及吃就跑来看望我。见我米缸里的米吃完了,红云、红宝两兄弟马上叫老吴称好谷子,连夜就上水碾房去把米碾好给我挑来……
这件事已过去了整整39个年头,但我却一直不敢,也永远不会忘怀!借此机会,我要怀着愧疚的心情,在再次向那些心像水晶一样透亮的质朴的苗族兄弟表示深深的歉意的同时,至诚地道一声:“谢谢”!谢谢您们用自己质朴无饰的行动,使我的灵魂得到一次无法用价值衡量的净化与升华!
二、苦涩
历经几年知青生活下来,我们这群原来吃饭斯斯文文,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知青”,早已磨练成吃两、三斤米的饭如同风卷残云,挑一、二百斤担仍然健步如飞的劳动能手--当然,为实现其中的转折,我们所吃过的苦、受过的累、发过的狠,大概也只有我们自己清楚了。尽管由于我们对于大部分农活都已能拿得起,放得下而不在话下了,但我们队上仍有两种让我至今想起都感到苦不堪言,十分后怕的农活--那就是犁冬田和放原木。
由于瓦窑地处高寒地区,一般打完谷子都是国庆节以后的事情,为了来年有个好收成,打谷结束,上完公余粮后就要把所有的冬田翻犁一遍。而我们所在的柴封山生产队,大部分农田都是终年积水不干的烂泥田--人踩进田里,不一会,水和着烂泥便会很快地淹没大腿甚至腰杆。10月以后的瓦窑大都已是雪飘霜冻的日子,要知道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我们还得上身穿着特别缝制的厚厚的棉背心(通常我们的苗族同胞连这个都没有!),下身穿着短裤,顶着肆意呼叫的寒风,一天十多个小时浸泡在齐腰深的冰冷刺骨的烂泥田里一干就是一月左右!那个苦哟,真不是人所能忍受的!……
一天干下来,我们常常拖着已冻得几乎失去知觉的双腿,扛着沉重的犁头,面对群山向苍天大声诘问:“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然后带着复杂的表情倾听自己的杰作:“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这,难道就是苍天让山神赐予我们的长长的答复?
殊不知待到春天真正来临,地处高寒地区的瓦窑的春天,等待我们的远不像诗人墨客在诗歌、散文中描绘的那样仅仅具有诗情画意般的浪漫色彩。如果说“犁冬田”带给我们的只不过是不能忍受的刺骨般寒冷的皮肉之苦,那么“放原木”不仅同样无法逃避寒冷带来的皮肉之苦,更为可怕的是,从事“放原木”这一农活,稍有不慎,便有可能被汹涌的山洪吞噬年轻的生命!
顾名思义“柴封山”有着特有的森林资源--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在一般的生产队每个劳动日价值不过1、2毛甚至几分钱的情况下,就是靠着它,我们换来了每个劳动日价值6、7毛钱的高收入、高效率--无论是山上的积雪未化、水中的坚冰未融,还是滂澎的暴雨下过不停;也不论是傍晚还是凌晨,只要春雨滂澎、山洪暴发,队长便会迅速召集队上的男性青、壮年组成放木队,借助暴发的山洪巨大的力量,把隔年农闲时砍倒、锯断的有一、两人合围大小的原木“流放”到大队所在地--地所。因为大家都知道山洪具有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特点,若不冒点危险,紧紧抓住这一稍纵即失的机遇,只要稍有懈怠,闭塞的交通现状,就有可能使当年每个劳动日价值6、7毛钱的高收入、高效率打了水漂。
在“放原木”的过程中,由于河床狭窄、怪石林立,落差极大,汹涌磅礴的山洪常常将笨重的原木堆集于河床狭窄的滩口处,造成“堵车”。此时必须有人迅速跳进河中去履行“河中交警”的职责:将堆集在一起的原木依次“调度”开,让它们有次序、守纪律地顺利通过河床狭窄的滩口。从小在乌江边长大、水性较那些只会点“狗爬稍”的村民好了许多倍的我,自然成为队长指派为“河中交警”的首选人物。于是,喝上几口红苕或青杠子酒以抗寒冷,系上一根粗大结实的尼龙绳以保安全,手握丈八长矛--竹竿一端捆绑上锋利的抓丁,带着全队男女老少一年的希望,便义无返顾地跳进冰冷刺骨的河水中去履行“河中交警”的职责!
我何尝不知道,在“调度”原木时,只要稍有不慎,汹涌的山洪便有可能裹挟着笨重的原木,将自己冲入滩底,上演一出或被怪石夹住,或遭原木砸死的人间悲剧--这,岂是那根企图维系我生命安全的区区尼龙绳所能抗衡得了的!